http://www.wangxiaoxin.net
 辛普森太太登上了Playboy封面,正如英国女王给夏洛克·福尔摩斯授爵。福尔摩斯之于英国,就像辛普森一家之于美国,一个绅士风度,一个没心没肺,这是两国人民的精神象征。若在全球范围,福尔摩斯的影响力恐怕比辛普森一家还要大些,毕竟流传的时间在那里摆着;对我的影响力就更不用说了。
辛普森太太登上了Playboy封面,正如英国女王给夏洛克·福尔摩斯授爵。福尔摩斯之于英国,就像辛普森一家之于美国,一个绅士风度,一个没心没肺,这是两国人民的精神象征。若在全球范围,福尔摩斯的影响力恐怕比辛普森一家还要大些,毕竟流传的时间在那里摆着;对我的影响力就更不用说了。
其实我看的第一本侦探小说不是福尔摩斯,而是一本叫《希腊棺材之谜》的东西。小学的时候课外图书贫乏,于是妈妈每到暑假就让我去她一个朋友的图书馆里借书。在没有有线电视没有网络没有手机的年代,夏夜的蝉鸣声中,捧着本厚厚的小说在客厅的日光灯下阅读差不多是我假期最愉快的事件之一。耳边爸妈还在讨论着今天的菜价,而我的思维已经到了一个奇妙的世界中。故事的前一半对于读小学的我并不有趣,那个过于陌生的世界在我面前更加乏善可陈;然而当看到中段侦探峰回路转的推理和精彩纷呈的大逆转时,我彷佛突然一下子明白了什么是侦探小说,那种既让我感觉有些惊悚又刺激的感觉真是太好了。我花了一个晚上读完这本小说,从此知道了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做侦探小说的东西。
这本书在侦探小说历史上的地位并不低,但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读者中的知名度远不如福尔摩斯。作者埃勒里·奎因(Ellery Queen)是弗雷德里克·丹奈(Frederic Dannay,1905-1982)和曼弗里德·本宁顿·李(Manfred Bennington Lee,1905-1971)这对表兄弟合作的笔名,他们相差九个月和五个街口,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侦探推理小说的集大成者(史上最成功的合作搭档),共创作了50多部侦探小说。《希腊棺材之谜》是他们许多“谜”系列中的一部,其他的还有《罗马帽子之谜》(处女作,1929年)、《弗兰奇寓所粉末之谜》(即《法国香粉之谜》,1930年)、《荷兰鞋之谜》(1931年,)、《希腊棺材之谜》(1932年)、《埃及十字架之谜》(1932年)等等,算是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之后的第三代侦探小说作家。他们的侦探小说富有美国风味,是上个世界那个极度繁荣、纸醉金迷的世界的缩影。
说完了第三代,现在来说说第二代作家的代表阿加莎·克里斯蒂。她几乎没有失败的作品,每部都很精彩,拍成的电影也是几位著名小说家中成功率最高的。她的长篇作品很多,大部分都很有新意,既不遵从前人的规律也不落自己的窠臼,精品很多。我第一次看她的书是在大学第一个月的某日下午,当时我们全体文科生被发配到称为“高四”的昌平园,而高考带来的疯狂学习热潮还没有褪去,那个乏善可陈的图书室里充满了中学生上自习的气氛。虽然这种气氛只持续到了当年的国庆,但已足以让我在那个下午找不到任何一个座位,只能坐在阴森巨大的书架后面的台阶上,看完了《东方快车谋杀案》。
那个下午,我整个人沉浸在从疑云重重到真相大白的快感之中。更让人惊喜的是,虽然这只是一部侦探小说,但阿加莎对每个人物的描写都极为立体,我记得我看到那个瑞典女佣时,脑海里出现的形象就是后来英格丽·褒曼的扮相。当我从书中抬起头来的时候,已经是日落西山了,有个不认识的男生走到我面前,说:“同学,那边有座位了,你去那边坐吧。”
这是我上大学感受到的最初的愉快,虽然我已经不记得那个同学是谁了。
之后我又看了阿加莎的很多书,《荒岛十命》、《尼罗河上的惨案》、《纸牌》,都是很好很好的,但给我留下最初印象的,还是《东方快车谋杀案》。我永远记得豪华的东方快车的夜晚,有个女人穿着龙纹睡衣的袅袅婷婷的背影,那场景让我大学期间每次坐卧铺回家的时候,都不自觉地想起这一幕。
下面要说回福尔摩斯了。最初接触到福尔摩斯,是在中学的时候,看完埃勒里·奎因的书,就开始借福尔摩斯来看,虽然之前听过他的名字已经很久了。我看的第一篇是《巴斯克威尔的猎犬》,或者《血字的研究》,或者《四签名》,不记得了,总之是那几篇中的一篇。之后,我看完了基本上福尔摩斯所有的故事,一共大约六十篇。柯南道尔的贡献,我想主要还是在于他创造了这样一个代表不列颠品味和风度的人物,以及开侦探小说先河的推理模式。看过福尔摩斯的人,没有不为他翩翩的风度、智慧的头脑和冷酷的作风所倾倒的,最后一点放在当代社会里,就是所谓“酷”。这几点在1970年代BBC所拍摄的电视剧《福尔摩斯探案集》中都被一流演员Jeremy Brent表演得出神入化,当然演员自己的贵族出身和他本身的高贵气质也大有帮助。
我觉得对福尔摩斯和华生的气质和他们俩的关系阐释得最好的是这个被评为“最好笑”的笑话:
英国著名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和他的助手华生医生在一次探险中搭起帐篷露宿。半夜,福尔摩斯醒了,随后他推醒了华生。
福尔摩斯:“华生,你看那满天的星斗,你能告诉我有何感想吗?”
华生:“啊,你看,这夜空太美了!看到那成千上万颗星辰,我想,如果在这无数恒星中,哪怕只有很少一部分有行星,这些行星就可能与地球类似,即使只有很少的行星与地球类似,这些行星上就可能有生命。”
“华生,你这蠢才,”过了一会儿,福尔摩斯说:“有人偷了我们的帐篷……”
这个笑话真的让我笑了好久。现在看起来,他们的性格、关系、智慧,在这短短的几十字里真是淋漓尽致啊。
在2010年BBC新版的《21世纪福尔摩斯》(Detective Sherlock)中,新生代演员Benedict Cumberbatch在这些优雅风度和表现气质的小动作上也是对Jeremy Brent一脉相承的。在电视访谈中,扮演华生的演员Martin Freeman说,当年柯南·道尔塑造福尔摩斯时,是把他作为一个非常现代非常先锋的人物放在当时的时代中的;所以我们现在把福尔摩斯放在当代社会中,他应该还是当代社会的潮流和领军人物。平心而论,看福尔摩斯用飞快的速度敲键盘、发短信是件温暖的事情,彷佛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一样。而熙熙攘攘的伦敦大街也没有改变:百年前的出租马车变成了出租车,伦敦的大街小巷还是一样又绕又堵;华生一百年前是阿富汗回来的军医而在一百年后,这个帽子竟然还能天衣无缝地扣上,日不落帝国你到底在中亚的泥沼中纠缠了多久啊。
福尔摩斯是第一个让我有创作冲动的故事。高中某个无聊的傍晚,我趁爸爸妈妈散步时在练习本上写下了我的第一篇侦探小说,照猫画虎塑造了某个无所不能的大侦探,竟然还靠着拙劣的文笔把故事讲圆了。现在想起来,这篇代表着我“处女作”的小说应该也被历史的洪流卷进了某个造纸厂的制浆机,变成了一团白色的浆糊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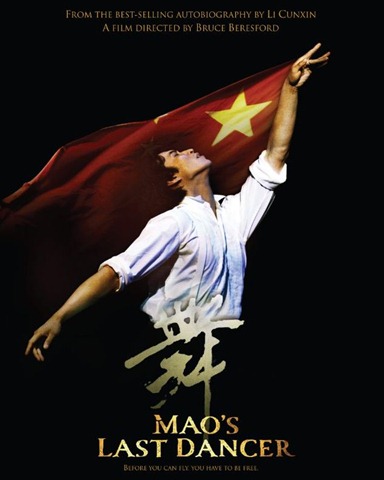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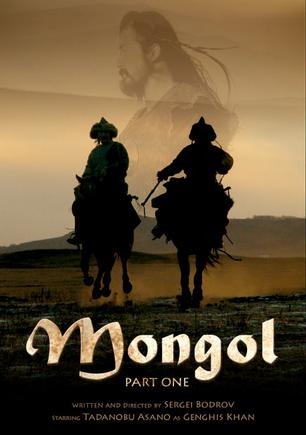

 周五的晚上,一群人在打麻将,昏暗的光线,San Diego七十七年来最冷夏天的夜风从门缝里飘进来。我坐在他们后面,开着Little Ashes的碟,从Blockbuster借的,半夜十二点之前再不还就要罚钱。
周五的晚上,一群人在打麻将,昏暗的光线,San Diego七十七年来最冷夏天的夜风从门缝里飘进来。我坐在他们后面,开着Little Ashes的碟,从Blockbuster借的,半夜十二点之前再不还就要罚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