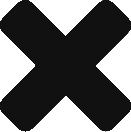-
Recent Posts
Recent Comments
Categories
Archives
- April 2020 (3)
- January 2020 (6)
- December 2019 (4)
- November 2019 (1)
- October 2019 (31)
- April 2018 (3)
- March 2018 (4)
- January 2018 (2)
- December 2017 (3)
- November 2017 (1)
- October 2017 (6)
- May 2017 (1)
- April 2017 (1)
- March 2017 (15)
- July 2016 (2)
- May 2016 (2)
- February 2016 (4)
- December 2015 (1)
- November 2015 (3)
- October 2015 (6)
- September 2015 (3)
- August 2015 (1)
- July 2015 (1)
- June 2015 (5)
- May 2015 (1)
- April 2015 (1)
- March 2015 (10)
- February 2015 (1)
- January 2015 (6)
- December 2014 (2)
- November 2014 (4)
- October 2014 (3)
- September 2014 (3)
- August 2014 (4)
- July 2014 (2)
- June 2014 (1)
- April 2014 (2)
- March 2014 (3)
- February 2014 (4)
- January 2014 (1)
- December 2013 (3)
- November 2013 (9)
- October 2013 (2)
- September 2013 (2)
- August 2013 (5)
- June 2013 (1)
- May 2013 (3)
- April 2013 (2)
- March 2013 (2)
- February 2013 (1)
- January 2013 (1)
- December 2012 (5)
- November 2012 (3)
- October 2012 (6)
- September 2012 (9)
- August 2012 (4)
- July 2012 (10)
- June 2012 (11)
- May 2012 (4)
- April 2012 (5)
- February 2012 (4)
- January 2012 (6)
- November 2011 (5)
- October 2011 (4)
- September 2011 (1)
- August 2011 (4)
- July 2011 (3)
- June 2011 (4)
- May 2011 (1)
- April 2011 (6)
- March 2011 (11)
- February 2011 (4)
- January 2011 (12)
- December 2010 (9)
- November 2010 (11)
- October 2010 (6)
- September 2010 (4)
- August 2010 (9)
- July 2010 (9)
- June 2010 (6)
- May 2010 (15)
- April 2010 (10)
- March 2010 (11)
- February 2010 (13)
- January 2010 (15)
- December 2009 (19)
- November 2009 (17)
- October 2009 (20)
- September 2009 (17)
- August 2009 (20)
- July 2009 (9)
- June 2009 (6)
- May 2009 (12)
- April 2009 (14)
- March 2009 (7)
- February 2009 (8)
- January 2009 (10)
- December 2008 (9)
- November 2008 (15)
- October 2008 (18)
- September 2008 (11)
- August 2008 (10)
- July 2008 (6)
- June 2008 (14)
- May 2008 (5)
- April 2008 (11)
- March 2008 (7)
- February 2008 (10)
- January 2008 (8)
- December 2007 (10)
- November 2007 (7)
- October 2007 (11)
- September 2007 (9)
- August 2007 (3)
- July 2007 (10)
- June 2007 (2)
- May 2007 (5)
- April 2007 (8)
- March 2007 (8)
- February 2007 (4)
- January 2007 (4)
- December 2006 (7)
- November 2006 (6)
- October 2006 (9)
- September 2006 (10)
- August 2006 (11)
- July 2006 (9)
- June 2006 (12)
- May 2006 (7)
- April 2006 (22)
- March 2006 (8)
- February 2006 (11)
- January 2006 (9)
- December 2005 (10)
- November 2005 (13)
- October 2005 (8)
- September 2005 (8)
- August 2005 (10)
- July 2005 (16)
- June 2005 (5)
- May 2005 (14)
- April 2005 (2)
Category Archives: 日记摄影
七苦(上)
七苦 (一) 躺在手术室的病床上的时候,我突然像某个产经上说过的那样,产生了强烈的想听《短歌行》的欲望。《短歌行》是怎么说的来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四字一言,锵锵有力,适合对我当时急需勇气的心情。麻醉师开始给我打针,在我的肚皮上戳戳指指,直到我下半身彻底失去知觉。我从push了三个小时的亢奋中解脱出来,随即感到的是抑制不住的疲倦和困意。我哆哆嗦嗦地问护士:“May I sleep now?”我以为一昏睡过去就是陷入万劫不复的昏迷。在得到肯定的回答的时候,我反而不能入睡,那种被双重麻药麻醉的痛苦是比宫缩和push更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虽然不痛,但是你能听到周围所有的声音和说话,但眼睛就是睁不开,也无法做出任何回应,我甚至不知道bird是不是在我身边。我只觉得平时惜字如金的ob和麻醉师在不停地聊天,但我却无法听懂他们说的任何一个字;同时有东西在我的肚子上不停地戳戳拉拉,但我却无法判断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当我听到我要被拉去剖腹产的时候,我难过得几乎要掉下眼泪来。我心里默默地说:娜娜,妈妈对不起你。 (二) 2007年冬天,我在拥挤的春运中奇迹般地买到一张票,连夜赶回阴冷的故乡。在火车站空旷巨大的台阶上,来接我的父亲告诉我,外婆已经在昨天夜里去世了。那一刻,我积蓄了一整天的泪水不受控制地流下来。当我回家看到她躺在床上冰冷而无生气的面容时,我觉得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这与我躺着产床上,等待被拉去剖腹产的感觉是相似的。一个小时前,我问bird,我是否还能凭自己的力量生出来。Bird很快地回答,能,然而我心里听到的答案是否定的。这么多年,我早已能从他的话音中听出他实际的想法。 生命的来和去其实都是一样的,那种命运的巨大的力量让你不由自主地被牵着鼻子走。你没有办法掌控过程,只能默默地躺在那里承受纷至沓来的各种力量。没有任何人可以信任,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和你一样感同身受。我觉得肚子里的孩子是可以感同身受的,可是她还不能与我分享。 娜娜被拽出来的时候,我是听到哭声才意识到我原来生完了孩子这一事实的。从巨大的昏迷中挣扎着睁开眼睛,我看到一个血丝呼啦的婴儿被高高地举在半空中,高过所有人的头顶。像是展览,又像是鼓励,给整个手术室严阵以待的医生、护士、麻醉师和各种工作人员的鼓励,更是给母亲的鼓励。当时我唯一的意识是,会哭说明健康。然后我闭上了眼睛,重新失去了意识。 当娜娜被洗好包裹好,第一次被放到我怀中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竟然是好不好看。在惨白的日光灯下,我尽力用最客观的标准去评判,也只觉得她特别好看。我只说了一句:“She is beautiful”便重新昏死过去,昏死之前听到旁边两个护士忙不迭地点头附和说“Yes, Yes, she is.”美国的护士就是这点好,无论你说什么或者有什么过于自信的想法她都会说“Well done”,全然不顾事实如何。 后来我发现在我重新昏过去之前护士帮我们拍了一张照,那是我们一家三口的第一张照片,也是最完美的一张。 (三) 10年的某一天,我冲到药房买了两个最贵的验孕棒。只用了一个,一分钟不到,清晰的“Pregnant”便出现在显示屏上。Bird上班去了,家里空空荡荡地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从来没有觉得非要孩子不可的我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我有一个孩子了,我会有一个孩子!九个月之后我就能领一个孩子回家了! 当然,当时我从来不知道怀孕是件艰难的事情,更不知道生孩子和养孩子的艰难。这艰难不 仅是体力上的变化,更是心情上的担忧。不敢多运动,放弃了所有的化妆品,难受的妊娠反应让我只能吃没有味道的subway和沙拉,在考GRE的时候还要忍着呕吐的感觉,这些都是小事。但头三个月一直spotting,每次都让我觉得心里一阵发凉。直到看到长手长脚的娃娃愉快地在B超图像里动,我们才放下心来。 以前,我一直觉得小宝是个男孩子,我们买了个蓝色的小海马,给肚子里的它听音乐。这是我们给它买的第一个玩具,为了奖励它早早地让我感到胎动。第一次感到胎动的感觉是奇妙的,那时候它还真的很小,胎动很轻,像小鱼在你肚子里吐泡泡。后来激烈的胎动简直像要把你的肚子给捶破,怎么教都不管用。 大B超的时候,B超师说“是个女孩”的时候,我还没有反应过来,花了好几分钟来接受这一事实。之后是疯狂地翻书取名字,这件事一直到出院前deadline的最后一分钟才定下来。
Posted in 日记摄影
Leave a comment
回乡记
蓝灰色的天空。北京的冬天。枯树。两年前从来不堵车的机场高速这会儿出了T3就开始堵车。火锅间的热气氤氲。见的人,说的话,八卦的故事都和两年前一样。满是灰尘的家。各种家具和家用的尺寸都好像小了一号。不热的暖气,倒时差的半夜,半梦半醒之间的那些人和事。灯光明灭。 由于后半个假期都在打电话和邮局吵架,打各种各样的出租车穿梭于派出所-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大使馆-邮局之间重办被EMS寄丢的签证和护照,北京的景色我已无暇顾及,虽然即使有暇顾及,也是被车流和喇叭声所占据。只是在一天路过故宫的后门,透过车窗看见角楼的飞檐翘角,世界仿佛静止了一瞬间,在冬天的温度中,一切的颜色都变得不明显起来,灰色中角楼的轮廓分外明显,前景和背景都是空无一物的深深浅浅的灰色。每个人走过这里,都会多看两眼吧。而我从第一眼看到它们到现在,已经有13年了。 北京的生活像快镜头一样从我眼前掠过,没有亲人,我不知道哪里才是自己的家。有时候觉得北京是,可是到了机场一个人孤独地拎着行李出机场,又觉得想回美国。回了美国,出机场还是一个人扛着六十斤的行李上下楼梯……我既不能反认他乡是故乡,也不能确认哪里才是真正的故乡,恐怕真的只有像无脚鸟一样飞机,漂泊在半空中了。 我无暇看到北京的天空,只记得美联航的机长在降落北京前说的一句话:“Welcome to Beijing. This is a beautiful day.”
停不下来的生活
周日的午后,暂时没有事情,在一堆group meeting+presentation+assignment+homework+reading+competetion…中得以五分钟的喘息。这个博客也几乎要废掉了,这唯一个私人的时间。有时候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离开家庭,离开女儿,离开祖国,离开得心应手的工作,独自一个人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做着不知道对将来有没有用的事情。这个遥远的北方,太阳四点钟就落下去了,黄黄地像个蛋黄。 十年前我也许会喜欢这样的生活吧。可是现在觉得自己像一个停不下来的车轮,不停往前,不知道是被别人推着走,还是自己的惯性。经常对自己说生命在于过程而不是结果,可是现在做的事情完全相反。为了一个不知道在哪里的结果,放弃了生命中所有的好风景,值得吗? 也许是永远没有答案的,因为永远都在这样不停走下去。时钟在走,秒针滴答。窗外的世界黑下来了,最后一缕阳光折射在几十年前发黄的老建筑上,呈现出一种奇妙的光芒。我知道外面是大风,也许还有雨雪,可是这光芒此刻是凝固的,静止的,与建筑外墙的线条一样,笔直而带有微妙的花纹变换。 我想我是想家了。
威斯康星的群鸦
在Van Galder的堪比卡车还高的大巴上,窗外群鸦成群地飞过玉米地。由于地势的开阔,云朵好像特别低,灰白的云层下面是低矮的灌木,叶还未黄,而玉米已经被收割完毕,留下大片黄色的空地。当年梵高要是来这里,也许能画出不一样的田野。 相比于加州的单调,中西部广大的农业州的风景则相当有层次。这里有树,有水,有黄叶,有风,有雪,有季节。相比之下加州的天气真是如永动机般无聊!好像某篇连载的科幻小说《异海》中写的那样,只有一成不变的永恒的极端。 从伊利诺到威斯康星,从西北到麦迪逊。最早知道这个地方是从高中某本《我们学英语》之类的杂志上看到的封面照片,白雪皑皑笼罩着静谧的校园。空气的凝固不单因为寒冷,还因为远离尘嚣的世外之地。多年不见的朋友来接我,在麦迪逊的校园里散步,看小本科生们的兄弟会姐妹会标,人人都穿着红色的校服去看橄榄球赛。这是九月中一个不忙的周末,天气还没有变冷,然而空气中已有凉意,不怕冷的美国大妞还穿着背心和背带裤,我则已经穿上了在加州时的最厚的衣服。小镇由State Captical广场为中心呈星形发散出来,两个小巧的湖散落在一旁。虽然街上也有人,校园里也有人,可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寂寥,这种寂寥在地广人稀的加州都没有过。加州是火热的,不安的,而这里是缓慢的,孤独的。 在这里生活的人是耐得住寂寞的。
紫校橄榄球纪事
橄榄球确实激动人心,在电视上看就已经如此,更别提现场的群情激奋。和一堆小本一起坐在紫色的海洋里,在几万人的Ryan Field为自己的学校加油,本身就是一件能提高学校自豪感和体育意识的事情……中国的学校什么时候来这么一下就好了。可惜百年名校们除了修个大讲堂,根本没体育场什么事,地方不够,意识也不够。体育给人带来的感觉是无以伦比的,几万人为一个队加油呐喊的壮观和温暖是人类崇高的极限希望。 昨天是Homecoming parade,老校友们拖家带口地全来了,在停车场里打开后备箱,拖出烧烤架,跟儿子儿女说,这就是你爹你妈曾经上过的学校!相对而言,football之前的tailgate就更像一场狂欢,男男女女在后备箱旁边使劲喝酒,仿佛生怕不能把自己灌醉去看令人难以接受的比分。果然,上半场还略微有领先主场优势的Wild cats下半场一分未得,难看得大家纷纷在比赛结束前就提前离场,结束了冬季到来前最后一个温暖周末的夜晚。 里三层外三层的紫色夹克、帽子、围巾、手套,还有脸上大大的N字,是同学们用冰棍加颜料互相创作的激情。大家在紫色的洋流中走回家和地铁站。这是我们的颜色。这是我们的节日。
美国东,美国西
在加州两年没有生过病的人一来芝加哥就得了感冒——这里的秋天行进的速度就像快进的录像带一样。昨天望下去楼下的树还是满树红叶,今天就已经落得满地纷纷,估计到不了周末就得叶尽枝黄,提前入冬。一周前还是黄绿相间呢。 加州真好。在的时候不觉得,离开了才知道,除了植被难看一点,加州的气候和温度是哪里都比不上的。在这样的气候下代代生活,加州人民果然是美国人民中最没心没肺的一群。刘思达说美国人民越往西越傻,这话不假。芝加哥人民走在路上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的样子,据说这叫“pessimisticly aggresive”。地铁年久失修,卫生间连坐垫纸都没有——这是旧美国,相对于加州的新美国,简直是两个国家。 这里还不是美国东,最多只能算美国中。Rachel说美国中西部和加州是英语口音最淡的两个地方,但芝加哥除外。南方人民口音更重,但我还没去过。也觉得想看世界的心愿不是那么强烈了。在看过那么多地方之后,还有哪里比家更好呢? 来了之后像疯狗一样的时间表,买家具,安顿行李,POP,报道,各种Orientation和免费午餐,聚会,认识新人,上课,新老师,作业,阅读,小组讨论,看朋友,看博物馆,看音乐会。然后又是作业,算术,统计,考试,小组讨论,案例分析。听讲座,听上届学生的经验。图书馆。办公室。教室。买菜,做饭,再写作业。 一个月就这么过去了。
周四的Famers’market
周四照例阳光明媚,和妈妈爸爸去UTC的Famers’ market。娜娜是我们的小跟班,到哪里都得带上她。她坐在小车里看鲜花着锦生蚝烹油。其实这世上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是一样,不论是她头顶上各种各样的树叶还是透过树叶缝隙的金色阳光,无一不是新鲜的。婴儿真好,能看到所有新鲜的东西。 农夫从海里捞上来海胆卖,5元一只,现场吃8元,真正生猛。海胆放在冰上,刺还在缓慢地动,让我想起上周海洋世界里面看到的章鱼馆里的稀奇动物。还有生蚝,oyster,可以做成lemon pepper和spicy的口味。卖蔬菜的墨西哥小伙子彬彬有礼,黄瓜1块钱5根。还有卖小吃的大妈,卖帽子的老爷爷,不遗余力地推销给小宝带的太阳帽。美国做生意的人就是这点好,不卑不亢,像和邻居交谈,不像五道口的小贩,眼里都透着精光,一副只要把你钱包掏空损失点尊严没什么的架势。这种平等的姿态让我更同情看起来没什么生意的帽子爷爷。在蔬菜海鲜市场上卖帽子,可能确实不太恰当。我很想照顾他的生意,可惜太贵了。但也许根本是我多想了,确实有很多人在农贸市场上买帽子呢。 最近同情心泛滥。微博上真一条假一条的留言,看了难受,不看又觉得不与时俱进。我真讨厌微博这个东西,从形式到内容都混乱无比,简直是群魔乱舞。形式混乱败坏心情,内容不辨真假败坏胃口。打着公共空间的幌子,全是流言谣言的温床,似是而非的知识,伪科学的观点。什么阅读习惯,什么高尚精神,全被抛弃了。 于是赶紧回来写点字,仿佛口渴的人要喝水而不是可乐。当然博客也是短平快,可和微博比起来,起码算是写字了。娜娜睡去了,我也要睡觉了。南加的最后一个夏天,太阳底下本无新鲜事。
夏日
是不太热的夏日的午后。房间的百叶窗透进来若有若无的白色光线。 做了很长的梦。梦见自己生完孩子从昏迷中醒来后,花了很长时间想“自己”是在“我”的身体里,还是在“母亲”身体里。 一睁眼,看见nana的小手放在奶爸的身上蹭啊蹭。房间里弥漫着奶香。 厨房里的煎锅上,一条死了的鲫鱼翻着大白眼,躺在黝黑的锅里,状如八大山人笔下的鱼鸟画儿。
Posted in 日记摄影
Leave a comment
作为城市之王的他们
前几天有一篇文章,是描述中国的快递员的,说他们的手可以轻易摸出快递的u盘是否金士顿4G,或者标书的厚度精确到页。在国内时,每天上班除了同事、客户和供应商,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快递员了。他们的自行车像闪光的鱼一样在城市的车流中游走,他们闪烁的目光背后藏着深沉的秘密,他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举动却不会告诉你,他们递过来的包裹或者信封里是沉甸甸的机关。我们看到他们的容貌,知道他们的时间,却不知道他们背后的故事;而他们知道我们的,从名字到爱好,从职业到薪水,从人际交往到不可说的地下秘密。 这样的城市之王有很多,除了快递员,还有卖光盘的。他们在一周的某一天晚上准时来到加班的办公室,拎着拉杆箱无声无息地推门进来。早有内线带他们进入一个会议室,然后加班的人们仿佛嗅到了什么气息一样,逐一放下手中的键盘和鼠标,鱼贯而入那灯光明亮的地下市场。他们熟知我们的爱好,对每一部片的要求,上下或者续集,蓝光或者D9,你要的是塔可夫斯基而你要昆汀,上次你要的货广州那边还没到,这张盘你先拿去电脑上试试能不能播……这是比例行找饭辙更有意义的时刻,你看着日光灯映照的那一摞摞光盘,早已神游到了深夜的家用播映机旁喝一杯小酒的时光。 到了美国之后,人与人之间的隐私被保护得极好,我们通常不知道邻居是干什么的,然而快递员直到。在这里,快递员变成了更伟大的职业。他们高高在上,开着18轮的大货车在州际高速上穿行。他们的车门从来不关,他们停车的技术超一流,能把车轮停在离马路牙子不足5公分的地方。他们个个威武雄壮,人高马大,满脸的络腮胡子,穿着UPS或者Fedex的制服,敲起门来孔武有力,经常把屋内的人震得一愣一愣。等你赶去开门,只听到楼道的大门一响,引擎发动,斯人已来去如风,剩下一个巨大的牛皮纸箱横躺在你门口的草垫上,上面写着你的名字。 这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生活过了很久,久到我从他们的敲门声就可以分辨不同的人和公司。他们通常一人负责一个区域,他们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住户熟悉到连地址写错的包裹都可以投对的程度。长久以往,我大概能分辨出那个敲门震天的快递员大概是墨西哥裔,长得蛮横但其实说起话来轻声细语,而那个Fedex小哥应该是身材瘦小的亚裔,对,就像Fedex广告上的那个一样。我想和他们打个招呼,可是他们离开的速度总是远远快于我开门的速度,除非需要签字的包裹,而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所以我们继续维持不见其人的友谊,而这种友谊更多是单方面的——他们知道我们,而我们不知道他们。他们能从名字、订的东西和订的频率上分辨出来你家小宝是否快满一岁,或者这位单身女性又换了个男朋友,而我们——我们只能听到那年复一年的敲门声。 美国的城市之王还有送报纸的,虽然我对他们所知更少。在我的想象中,他们应该骑车在薄薄的晨霭中穿行,在这个城市即将苏醒之时把一摞摞报纸准确地投递——不,应该说是“扔”到订户的家门口。我这个印象的得来是因为从我家的地势看去,这摞报纸是从一楼直接扔到我家三楼大门口的,从准度、精度和时间来看,那家伙从未失手。由于投递报纸的时间相对我的起床时间实在太早,所以这个想象一直没有得到证实。我曾经自己在一楼尝试扔过,完全不得要领。直到今天,这个想象得到了证实,因为妈妈来我家了。据她的证词,早起晨练的她站在楼道口往下俯视,只见一个家伙朝她笑,然后一摞厚厚的报纸“嗖”地向她飞来,她一手接住,还以一笑。听完之后,我脑海里出现了一幅活生生的武侠高手过招的场面,大侠与大侠对决,然后相视一笑,各走江湖。
Posted in 日记摄影
Leave a comment
一个欧盟能源专家的退休生活
Giovanni每次见到我,总是很严肃地和我讨论一些严肃的形而上和人类技术前景的问题。他是意大利人,在欧盟做过多年的能源专家,苏联解体后,总是被派到东欧的穷国去,帮助当地的能源部门与欧盟的标准接轨。他在布拉格住了好多年,又在布鲁塞尔住了几年,后来要被派到罗马尼亚去的时候,终于拒绝了,和他的美国妻子Anne回到美国来,在西岸的阳光下过起了惬意的退休生活。他和Anne是四十多年前被派到美国做能源电池时认识的,这使他最终放弃了意大利国籍,成为了一个带意大利口音的美国人。 Ann家是我见过的美国人里面思想最开明的一家,比起大部分保守的美国人,他们很随便地就接受各种政治和宗教观点,对中国的了解令人咂舌。在他们家做客,他们和爸妈谈起文化大革命,推荐他们看Mao’s last dancer;我想了想,如果反过来,爸妈能和他们谈谈肯尼迪遇刺和民权运动吗?肯定不能。Giovanni和我说意大利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历史悠久,机构浮肿,精英教育。他的中学也分文理科,文科要求学六年的拉丁语,至今还能大段背诵莎士比亚的台词。Anne就觉得很不解,为什么要背这些没用的东西,学这些死亡的语言? 我却很能理解,觉得这和我们背《岳阳楼记》是一样的。说到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他又拿出一本世界地图,查询SD和我们家乡的纬度。 Anne家最近爱上了中国茶,我去他们家,总是带一些乌龙茶或者绿茶。Giovanni得意地向我展示他的茶叶收藏,满满一柜子,难为他从美国的网站上买到邮购的中国茶叶。他和爸爸探讨泡茶的方式,有自动控制水温的开水壶,有沙漏,还有精确的量杯。他跟我说,美国人以前不喝中国茶,只喝英国茶(印度茶),红茶浓到分不清杯子里的是茶还是咖啡,苦得惊人。然后他详细介绍了红茶、绿茶和乌龙茶的发酵过程,顺便教了我几个英语单词。 Giovanni和Anne的家在La Jolla海边的半山腰上,客房里能看见海景,真正做到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Anne种的花花草草比比皆是,还摘下好几个橙子送给妈妈。后院里有一片空地是Giovanni体育运动的地方,最近他们迷上了一个游戏叫Bocce,是一种类似滚地球的意大利式球戏。Giovanni说他年轻的时候玩足球,后来打网球,再后来打高尔夫球,现在就只能打Bocce了,这球的运动量和中国的门球差不多。说话间他拿出一张纸,给妈妈图示他新换的膝盖手术示意图,两个语言不通的关节病患者进行了热切的交流和意见交换。